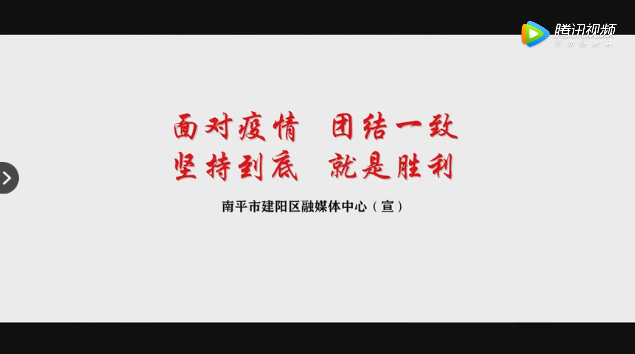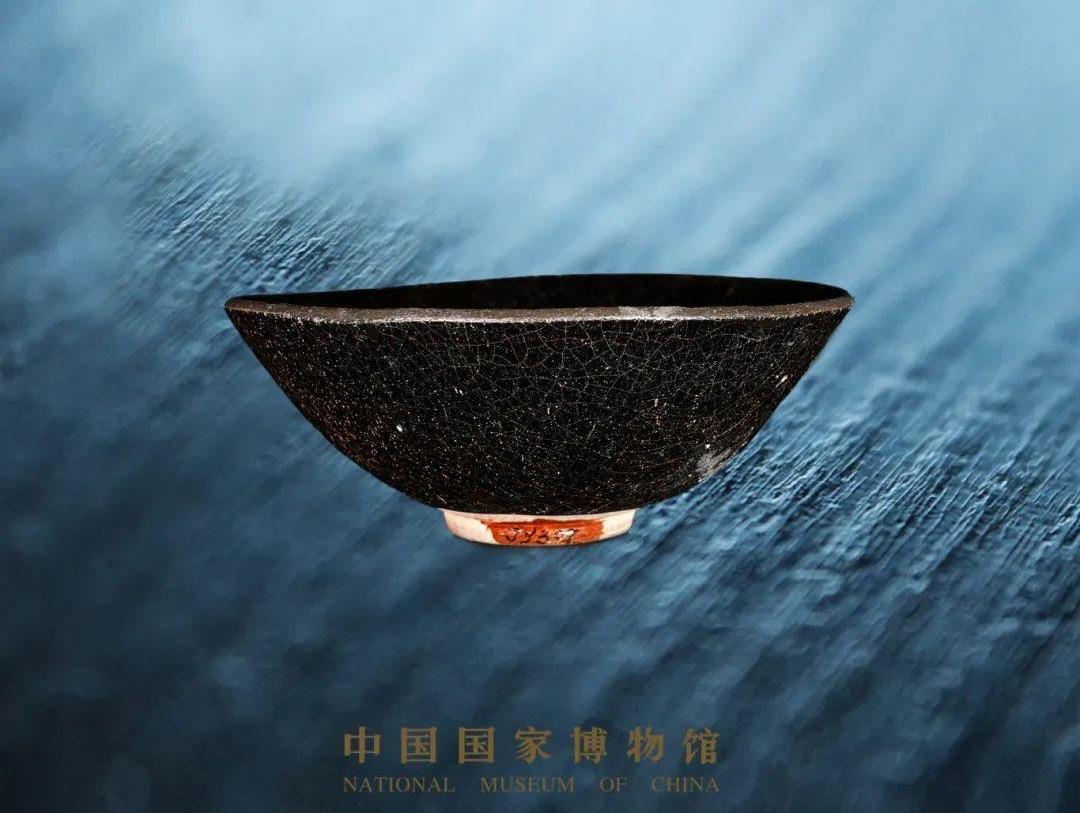记忆的麦田
| 2021-01-19 10:59:04 来源:今日建阳 责任编辑:肖练冰 我来说两句 |
分享到:
|
其实,麦子早已离开我的生活,但那段岁月,总在心的角落里占据着,不肯离去。每每回味起,姨丈翁和姨婆矮矮的小小的身影还会生动形象地浮现在我的眼前,像故乡这个有些模糊而遥远的词。 时光流过了那么多年,有些事早已忘记了,但我还能记得收割麦子的日子像饱满的麦粒般晶莹而美丽;记得那些带给我清香的麦穗。 记得我姨丈翁,人称矮伯子的有种麦子。那时正是搞生产队的时候,谁家里都不能有自留地,他因为是五保户而在伯公塬那里有一两亩地。也不知当时的五保户有些什么待遇,只知道姨丈翁每到墟日就会挑一挑青草药,迈着罗圈腿,一步步地走向五六里之外的墟上,卖一些钱来生活。 听姨丈翁说,他从前是有儿有女的,牵婚后,五六个孩子都莫名地相继病死,老婆也气死了。他老人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牵婚一定要算八字,八字不合就不能去牵”(牵婚是当地一种习俗,即让新娶来的新娘子,认一门干亲,这种人一般是婆家的兄弟或与婆家同辈的长辈)。成了孤家寡人的矮伯子就到我姨婆家里来。姨婆有一儿一女,那时儿子成家,女儿已出嫁。姨婆也是矮个子,长得和我外婆一样小小的,一米四都不到。 姨婆与姨丈翁两人都非常喜欢孩子,他们一起生活后,认了好多干儿子。姨丈翁要种那一两亩地时就叫上那些干儿子来,给他们饭吃,也让他们帮帮忙。姨婆与姨丈翁家里来干儿子时,我都会被叫去。种麦子,收麦子时我也会跟去。那里太好玩了,想割就帮着割两下,不想割就在那里玩。特别麦子打完后,就把麦秸铺开来,在那里打滚,翻跟斗。弄得一身泥草和汗水才回家。更主要的是他家的饭也吃得饱,有时一人还能分到一小块咸带鱼。 其实,孩子们大都是去玩,都是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,能做什么事呢?真正劳作还得靠那个和气、矮小、爱孩子的老头佝偻着腰背,用粗糙的双手来做的。麦子打好后,姨丈翁用小箩筐挑,孩子们用篓子提,一群人像蚂蚁抬蜻蜓样把麦子搬回家。而姨丈翁的那片给予我们欢乐的麦田,在他们去世后早已成了别人生存希望的地了。 他们在播种或收割麦子,我大都是坐在田埂上,晃着着双脚,在那儿咿咿呀呀地唱有关麦子的歌谣。因为我是女孩,又是早小的一个,我就是来玩的,来吃白饭的。而那时唱的童谣还记得一些,如:金麦子,金粒粒。能做饼来,能拉面……还有:天蓝蓝,麦黄黄,小囝囝,提竹篮。麦田里,忙呀忙。弯下腰,仔细看,一穗穗,一粒粒,捡满篮…… 流转的岁月,终是抵不过沧海桑田的变化,远去的麦田更像一场斑驳的梦。每次回家,站在村口,一任记忆的青苔爬满斑驳的老土墙,怀恋的是从麦子里飘出的特有香味。 |
相关阅读: